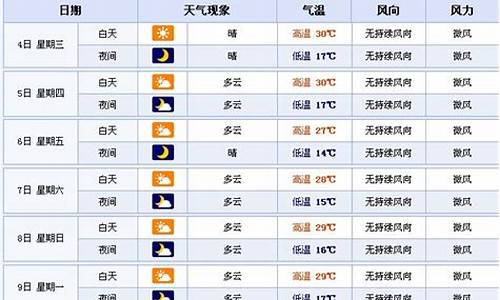导语:徽州的复名成了热门话题,各种争议层出不穷,在这雨季,一个残缺的徽州让一府六县的徽州遗民呼吁了30年,只是那30年前的雨在这秀美的古徽州越来越大,以下是我整理的描写徽州的散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无梦到徽州三月的天气,最美不过的是这江南缠缠绵绵的雨季。漫山遍野的新绿在微风的轻拂下,泛着跌宕起伏的波涛,仿佛是一弯洁净的海水,来回拍打着承载它的大地。七彩的花儿,装点成一只只形色各样的小船,在这绿色的海洋里泛舟航行,徜徉着的快乐美丽。
天空中常常飘着蒙蒙的雨滴,而却听不见任何一丝雨落的声音,只看见那轻盈的一滴落在新发的绿叶红花上,便使得这天然的绿和红显得那么的娇嫩欲泣。细雨缠缠绵绵的不肯离去,整个大地都被润湿,而被湿润的水气滞留在山间,遇着了清冷的空气,便蒸腾起薄如蝉翼的雨雾来。这萦绕着翠绿山色的雨雾,像是一层轻薄的灰白色面纱,遮盖了山色的谲奇,却也给这原本的美丽风景增添了几分神秘。远远望去,白色的雨雾飘荡起伏着,墨绿的山峦若隐若现,倒也像是神话中的蓬莱仙境。
天开神秀的无双胜景里,不知埋藏着多少才子佳人的纠葛缠绵。千百年来,也不知这块神秘的土地创造了多少惊世。
徽州人便世世代代生活在这样的人间仙境中。
用今天人的眼光来看,能够居住在这样天造的美景中,是羡慕也得不来的福气。可是上溯到千百年前,这里的人们却无暇眷恋这里的美丽。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的中国古代社会,似乎从来看重的都只有那些能够养育自己的良田耕地。但是看似广袤的徽州大地,拥有的却只是在崇山峻岭中可怜的一点点盆地,而美丽的山色里却难以种植金灿灿的稻米。
勤劳的古徽州人在河湖经过的狭小平地细心开垦着每一寸田地,但每年的收获却也只能勉强糊口而已,“衣食无忧”都成了一种奢求。
如世世代代的徽州人真的就只是过着这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那便永远也不会创造出惊艳后世、纷繁锦绣的地方文明。古徽州人从来都没有向命运屈服,因为他们骨子里拥有的不仅仅有坚韧不拔的精神,还流淌着锐利进取的沸腾血液。人们不甘于一辈子埋没在深山老林中去开垦贫瘠的立锥土地,他们要追求富裕,追求幸福的生活。于是纷纷立志外出闯荡,或是读书、或是营商、或是其他行当,总之是要走出大山。而最终的事实是,不服输的徽州人在他们从事的各个行业里都创造辉煌。
熟知历史的人都知道,徽商曾经在明清两代称雄全国长达四百年,这已然是不朽的。直到如今,那段辉煌的往事也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沉淀而化作历史的过眼烟云。当你来到徽州大地,来到徽商巨贾们留下的豪宅华府里,你便依旧能够感受到这里的深厚气息。
徽州的古建筑透露出的是一种秀外慧中的美。也许是因为徽州商人们从来不喜欢显露自己的财富,于是我们看见的豪宅也大抵都是“青砖黛瓦马头墙”这样的整齐划一的外表。而这朴素中透露出来的却是一种别样的威严和华丽。各不相同的室内的布局与装饰,却又直接彰显着主人的富足和品味。雕栏画栋的巧夺天工,玉石金器的陈设,亭台楼阁的雅致,花鸟鱼虫的点缀,无不投射出富商们娴雅的`生活情趣。而富丽堂皇的室内,却怎么也不会让你感觉一丝充满金银气息浓妆艳抹的俗气。这不仅仅是因为徽州商人喜欢风雅之物,而最重要的是徽商们骨子里流露出的文化气息。
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和崇尚读书的观念在古徽州也留下很深的烙印。可偏偏是天运不祚,耕地在徽州太少也太珍贵了,以至于“早耕晚读”的生活逐渐变成了一种幸福的理想。
徽州有句流传久远的歌谣这样唱到:“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不屈不挠的徽州人没有选择怨天尤人,他们懂得如果一味的守旧便意味着一辈子的贫困潦倒。于是他们笃信“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这样的格言,不顾当时社会舆论的鄙夷,走出大山,开拓商路,默默的耕耘这条发家致富摆脱贫困的唯一出路。
徽州古人们在崇山峻岭、断崖峭壁间披霜露斩荆棘,不畏死伤之艰险,以开尺寸之路。而此羊肠小道,上通苏杭,下抵闽粤,在祖祖辈辈的苦心经营下,最终达到往来商贾逐渐络绎不绝,贸易遂日趋发达空前局面,成为徽商发迹的黄金商路。后世人赞誉说,这是徽州人独有的一种“徽骆驼”精神创造的成功。“不服输、不怕苦”是这种精神里面最重要的部分。徽商成功的背后,蕴含着的血泪心酸也许只有真正了解这块土地的人才能够知道。
从某种意义上说,徽州人是被迫经商的,而他们骨子里始终向往着的却是读书人的生活。从古至今,这块神奇古老的土地可谓是钟灵毓秀、人杰地灵,皖省历史上很多赫赫有名的人物都出自这块风水宝地,其中不乏朱熹、戴震、胡适之类的学者大儒。
自宋代以来,历朝徽州府的状元及第比比皆是,以致世人称颂道“东南邹鲁”,“状元故里”,总总美誉,名噪一时。想比与富甲天下的豪迈财气,徽商们跟看重的却是“天子门生”的光宗耀祖。即便是在徽商显赫的明清两代,读书人取得的成功让纵使是家财万贯的巨商大股们也艳羡不已。
在封建社会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社会风气,是无论用多少钱也转换不来的深刻印记。徽州商人们崇尚文化书理,他们不会仅仅满足于在商界的驰骋逍遥,“读书”也是他们一直长期坚持的东西。徽商们常常是手不释卷,亦商亦儒,工于书画,俨然文雅士。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富起来的商人们在故里兴资办学,崇文重道,推己及人,使得徽州大地文风盛行。这也就是徽州商人和文人一直都是翘楚华夏的重要原因。
靠着勤奋和天资,徽州古人们在崇山峻岭里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文明印记。时光荏苒,物是人非。今时不同往日,任何的显赫辉煌的过去也可能化作尘埃被历史的长河冲刷掩埋。走在这里,踏着青石板铺成的古路,寻访曲径通幽的小巷和历经沧桑的石桥和依旧矗立的溪边码头,这些古老的遗迹都在述说着这里厚重的历史沉积。也许每一块石头,每一条小巷,每一座石桥和码头,背后都会有一个动人的故事。
千百年过去了,祖先们留下的这些东西却从来没有改变,人们依旧居住在祖先创造的环境里,只是增加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村落伴着河流井然有序的排列着,村子里的每一样建筑依旧还是鳞栉次比。虽然现在已经不可能像古人那样生活,但是传统却从来没有被抛弃过。现在的徽州人依旧跟过去一样,尊师重道,勤奋坚韧。
崇山峻岭的阻隔,也使得徽州保留了完整的古代气息。没有繁华都市的热闹喧嚣,只留下淡雅恬静的自然风韵。在这里,天人合一的哲学态度长久流传着,保证了人和自然的琴瑟和谐。
生活在其中,我们宛然发现,原来自己一直身处在中国国画里的乡村中,就和那笔尖留下的写意墨水一样,徜徉自由,无拘无束。我们逐渐明白,为什么会有无数的文人墨客不惜笔墨,赞美徽州的美丽,这份美丽也不仅仅是天造地设的风景,还有住在这美景里的人。于是我们也不难理解,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会发出这样的感慨“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走进徽州不是不想去安徽,也不是想去安徽;去安徽没有理由,不去安徽也没有理由;但还是去了安徽。
单位要组织出去旅游。有的说去安徽,有的说要去上海,有的说要去南京,有的说要去江西————“那就去安徽吧!”我想。我这样说,好象没有经过大脑,又好象经过深思熟虑。
四月的春天,满山遍野鲜花绽放。春天写满了天,绿透了山,填满了海;春天走进了乡村,也溜进了城市。春天写在人们的脸上,春光洒在游人的身上。我也混在游人的队伍中,放松一下心情,感受一阵春的气息,嗅一嗅花的芬香,抖一抖身上的灰尘,排一排心中的郁闷。
从衢州到屯溪,二个小时,我睡了二个小时。二十八个同事,二十八种心情,到过安徽的说安徽,没去过安徽的想安徽。三年前,我晚上从上海去庐江,呆了二天,然后又连夜从合肥回家。安徽也算去过,但对安徽没有形象,只觉得安徽人好客,安徽菜好吃。虽然没有游历过安徽的名山大川,但向往黄山,钟情徽派建筑,敬仰徽州商人智慧,尤其徽州商人背后的女人。其实在江南,在北方,在中国的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徽州的影子,我家的老屋也是徽派建筑,粉墙,青瓦,马头墙。
安徽是古安庆府和徽州府的合称。现在的皖南就是古徽州。徽州商帮,在明清居全国十大商帮之首,徽商称雄商界三百年,“无徽不成镇”,“徽商遍天下”。徽派建筑是中国古建筑最重要的流派之一。徽州的山川风景之灵气和徽州的工匠之智慧,徽州商人的财富和徽商文化,创造了徽派建筑,使徽州成为徽派建筑的博物馆。徽州的优美地理位置、发达的新安江水系和物产丰富的木材、茶叶等,成就了一代又一代的的徽商。
走进“桃花源里人家”的西递,就象走进明清民居博物馆;走进牛形古村落的宏村,就象走进“中国画里的水乡”;走进神秘的南屏,就象走进迷宫;走进千年关麓,才知道徽州商人的强势;走近棠樾的牌坊,透着寒气,坚硬冷峻、青苔斑驳的石牌坊倾诉着神秘厚重,震撼肺腑的故事————来到绩溪的龙川,这里诠释了1600多年的“风水宝地”。龙川村,东有龙峰耸立,西有凤山对峙,北有登源河蜿蜓而至,南有天马山奔腾而上。站在高处俯瞰,龙川村依青山傍碧水,龙川水绕村东流,村落象条船,村里有千回百转的古廊桥、有历经千年的胡氏宗祠、有一门三尚书的古牌坊、有千百媚的水街、有三江汇流的园林水口————那一座座牌坊是徽州人的精神家园,那古村落和古建筑是远古徽州的繁华和富贵,牯牛降的原始自然传递出徽州大地的久远、淳朴和原生态的珍藏,横亘黄山南北的新安江、太平湖,更增添了黄山水之灵秀。
对徽州商人的财富,对徽派建筑的艺术,对徽州工匠的聪明,对徽州自然风光赞叹不异的同时,我们更应该记住那些成功商人背后的徽州女人。
一个女人,一个梦,一世夫妻三年半;一条辫子,一副枷,沉沉噬尽风华。据导游介绍,在当地有这样一个传统:男孩子长到十四五岁便要出门从商,一去便是十几年,其间他可能会回来一次,迎娶父母为他选定的妻子。当婚礼结束后,男人就必须重新离开故土,外出经商。下一次回来很可能就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了。而他的妻子则只能留在家中侍奉公婆,育子读书————一片斜阳晚照,已无心对着明镜打扮装束。风流云散,袅袅摇曳的长裙在晚风里张扬着,琵琶声声催人心弦,凄婉悲噎,曲折缠绵,不知是否已穿过层层叠叠的飞檐翘角,传送到了千里之外,只是那一弯新月如昨日————直到晚年自己的丈夫衣锦还乡。徽州的古民居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高高的马头墙上只开一个一尺见方的小窗,因为男人们长期在外,担心家里“红杏出墙”,不让她们窥视屋外的男人,当然也阻挡了男人窥探深宅大院里寂寞娇妻的视线。久久地倚栏,只为追忆是刚泛青时的美好年华,含情是那时的缠绵,脉脉是今生的牵挂,如同那漫天飞舞的杨花再也进不了眼底,在粉墙黛瓦的小楼中极目远望,明月静溢,四时不同,只有孤灯依旧,丢不弃、抹不掉的仍旧是岁月的年轮,千载之下千年的梦,一觉醒来发已白,如霜雪,曾经的妩媚生姿,如断了线的纸鸢在天际里找不到踪影。
徽州留守女人并没有因为情感的煎熬、性的压抑、生活的苦寂而郁闷,因为她们的眼里从来没有放弃过冀盼。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之中的女人们,她们阐释生命的方式自然有着衍生于性别的执着与精彩。也许这是她们对丈夫忠贞不渝的爱情所致;也许是传统礼教和闭塞的穷乡僻壤使女人们对生命对自由始终处于一种蒙昧状态。正因为有这样的荣耀与信念的引领,这里曾崛起一群贤淑、内敛、坚韧、豪迈、忠贞、勤勉,浸润古徽州文化精髓的的女性。百年前的徽州文化鼎盛,徽州女人功不可没。
徽州商人、徽州建筑、徽州女人,并不是徽州文化的全部,但诠释着徽州文化。可这也不是我要来安徽的理由。我是带着内心的不安而思念安徽;带着不解而神往安徽。